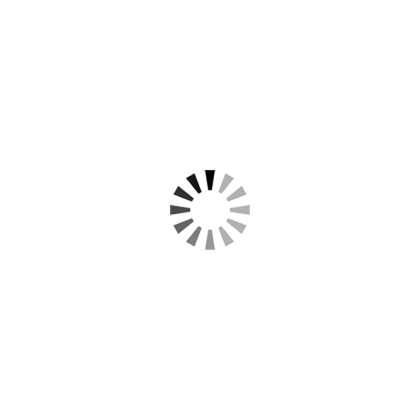我的四个假想敌ppt课件,我的四个假想敌
- 杂文
- 2022-04-19 14:30:14
- 8655

 摘自《就这样走到了故乡》-余光中
摘自《就这样走到了故乡》-余光中
第二个女儿优山在香港参加海外留学生联考,并将其分发给台大外语系作为第一志愿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不必担心我的四个女儿嫁给广东男孩。
当然,我对广东男孩没有偏见。在香港的六年里,我班上有许多可爱的广东青少年,他们很受老师的欢迎。然而,我不愿意让我的四个女儿都被那些“漂亮男孩”和“lak男孩”绑架。然而,想要结婚的女儿,更自由地说,是他们的自由意志,更神秘地说,是命运,那么为什么要担心作为父亲的得失呢?此外,在这件事上,母亲往往站在最前线,自然成为女儿的亲密顾问,甚至亲密的战友。战斗的目标不是他们的男朋友,而是他们的父亲。当父亲醒来时,他已经受到了来自双方的攻击,无法阻止大势所趋。
在父亲的眼里,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之前,因为那时她属于自己。在男友眼里,她最可爱的时光是在17岁之后,因为在这个时候,她就像一个毕业班的学生,一心想出去。父亲和男朋友之间有矛盾。对于一个父亲来说,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年幼的女儿更完美的了。唯一的缺点是,除非你用冷冻手术把她藏起来很长时间,否则她会长大,但我担心这是违法的,迟早她的男朋友会骑马或骑摩托车把她叫醒。
我没有使用太空舱的冷冻催眠。当我被时间逼迫时,太阳和月亮旋转着,又揉了揉我的眼睛,为什么我的四个女儿依次长大了呢。过去童话故事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,再也回不去了。四个女儿分别是珊珊、幽珊、佩珊和姬珊。它可以排列成珊瑚礁。姗姗十二岁时,九岁以下的佩珊突然对来访的客人说:“嘿,告诉你,我妹妹是个女孩!”这里所有的成年人都笑了。
曾几何时,即使是最幼稚的纪珊,也被时间的魔杖启发成了一个“女孩”。在黑暗中,四个“年轻人”偷偷溜了进来。虽然我踮起脚尖屏住呼吸,但我感觉身后有四双眼睛。像所有坏男孩一样,我的眼睛灼热,我的心错了。时间一到,我就会站在阳光下,假装虚伪,给岳父打电话。我当然不会回答他的。没那么容易!我就像一棵果树。我已经站在这里很多年了。风、霜、雨和露水在一切事物中都有份。为了换取许多水果,我不知所措。而你,偶尔路过的男孩,意外地伸出手去摘水果。你应该被滚滚土地的根绊倒!
最恼人的是,树上的水果看起来像是自动落入行人手中。树怪行人不得擅自采摘水果,但行人说水果刚刚掉下来,交给了他。这种事情总是内外兼顾才能成功。我自己结婚的时候,不是也有一个女孩为小偷开门吗?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”,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但那一刻也是,这一刻也是。同一个人过马路时讨厌汽车,但开车时讨厌行人。现在轮到我开车了。
多年来,作为肥皂和香水不变的原则,我学会了与五个女人在一起。沙发上没有袋子和面包卷。没人和我争酒。吴璐被戏称为“女生宿舍”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作为“女生宿舍”的管理员,不欢迎陌生人是很自然的,尤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。然而,我管辖下的女孩,尤其是前三个,一直“不稳定”,这让我想起了叶芝的一首诗:
 一切已崩溃,失去重心。
一切已崩溃,失去重心。
 我的四个假想敌,不论是高是矮,是胖是瘦,是学医还是学文,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,一一走上前来,或迂回曲折,嗫嚅其词,或开门见山,大言不惭,总之要把他的情人,也就是我的女儿,对不起,从此领去。
我的四个假想敌,不论是高是矮,是胖是瘦,是学医还是学文,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,一一走上前来,或迂回曲折,嗫嚅其词,或开门见山,大言不惭,总之要把他的情人,也就是我的女儿,对不起,从此领去。
无形的敌人是最可怕的。此外,我在光明中,他在黑暗中,还有一个来自我家的“叛徒”。这真的不可能预防。只是一开始我们没有及时冷藏我们的四个女儿,这样时间就不会被绑架,社会就不会被污染。现在他们太老了,不能回头;我的四个假想敌和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浑身长满了羽毛,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。
最好先开始。这件事应该在四个假想敌还处于婴儿期时解决。至少美国诗人奥格登·纳什建议我们这样做。在一首美妙的诗《女婴之父将要唱的歌》中,他说,在生下女儿吉尔后,他很紧张,觉得一个男婴正在某处长大。尽管他仍然困惑不解,口吐白沫,但他注定要在未来带走吉尔。
因此,每当父亲看到公园里婴儿车里的男婴时,他的脸都会变,他想,“会是这个家伙吗?”他以为自己是“我的梦想,如果耳朵还在幻想中的话”,就会解开男婴身上的别针,在滑石粉里撒胡椒,在奶瓶里撒盐,在菠菜汁里撒沙子,然后把头上游动的鳄鱼扔进婴儿车里和他玩,迫使他在深水和火中挣扎着娶别人的女儿。这表明诗人以未来女婿为假想敌是有先例的。
但为时已晚。正如纳什在诗中所说,不迅速做出决定,不采取非常措施,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今天的情况,历史书中的一句俗语,是“土匪深入!”在她女儿的墙上和办公桌的玻璃垫下,以前的海报和剪报,或者披头士乐队、贝丝和大卫·卡西迪的照片,现在都变成了男友。至少,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,这场战斗注定要失败。我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,这样的照片仍然被列为机密元素。它们要么藏在枕套里,依附在梦中,要么夹在书的深处,偶尔被证明是着迷的。我们面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24小时的礼拜?
无法测试这群形迹可疑的假想敌是何时、在哪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上的剩余房屋的。我只记得六年前搬到香港后,一群年轻的粤语演说家接管了军事围攻。至于战斗的细节,我得问问那些名义上守卫这座城市的女将军。我的“困惑的国王”再也弄不明白了。我只知道敌人的炮火一开始是对准我的邮箱的。那些歪歪扭扭的笔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可以猜到七分;然后是我家里的电话。“子弹落点”在我桌子后面。我的文学花园是他们的战场。一夜之间发生了十几起脑震荡。这些广东人的声音中有九种,我很难分析敌人的情况。现在我带游山回厦门街。轮到我妻子在另一端的广东军队抵抗了。我来了。只要我关注台湾运动员,任务就会轻松得多。
邮箱是否被攻击无关紧要,就像一部无声的战争电影。事实上,我更喜欢多情的青少年经常写情书,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练习写作,以免在电化教育时代浪费中文。可怕的是,手机被击中了。一串警钟把战场从门外的邮箱扩展到了书房的腹地。无声电影变成了立体声,假想的敌人正在用实弹射击。
更可怕的是,假想敌真的闯入了这座城市,变成了血肉之敌。它不再是想象和有趣的,就像在军事演习中的一场真正的战斗。真正的敌人看得出来。在女儿的招待会上,他占了沙发的一角。从那时起,两人窃窃私语,秘密交谈。即使脉搏相反,空气也太浓,全家都无法呼吸。这时,几个姐妹已经躲得远远的,谁都能看出情况不同了。
如果敌人留下来吃饭,空气会更紧张,就好像他在对着镜头摆姿势。在通常的鸭池餐桌上,四姐妹似乎在表演哑剧。就连筷子和勺子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,突然变得谨慎起来。知道闯入的男孩可能不是正确的女婿(谁知道现在女婴的十八个变化中的哪一个?),但我心中升起了一丝敌意。我也知道我的女儿就像一个成熟的瓜,总有一天她会掉下来,但我希望不要跟着我面前那个自负的男孩。
当然,这四个女儿也有自己的孩子
声明: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,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,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,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。
本文链接:http://www.ylslh.com/n/23844.html